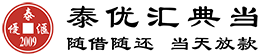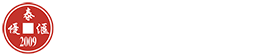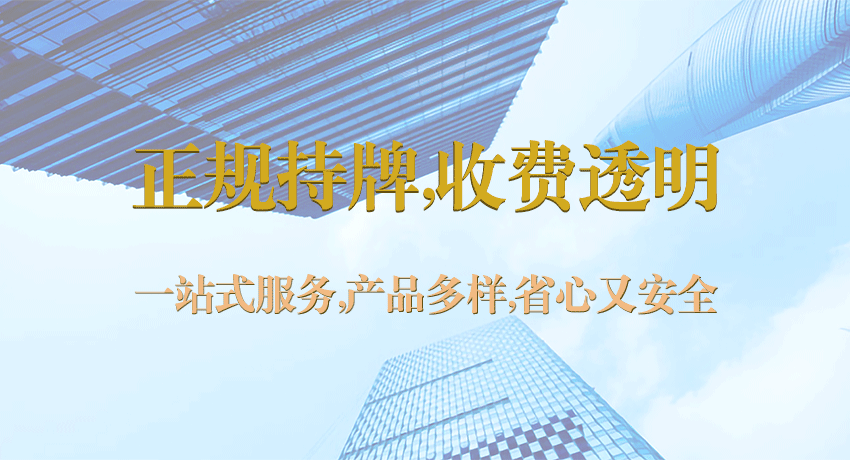車輛抵押借款合同范本(《車輛抵押借款合同范本》)?
導讀:機動車所有權人在機動車設定抵押的情況下,又將車輛質押給質權人,質權人又通過與他人簽訂“車輛轉(質)抵押協議”等方式移轉給他人,他人再次將該車輛進行移轉。上述車輛移轉方式在二手車交易中大量存在,當機動車被抵押權人或其他權利人行使權利時,最后一手受讓人權利如何保護,成為近年來法院受理案件的一個類型。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相關判例可知,全國各地很多法院均處理過此類案件,并且,裁判觀點也有很多不同之處,例如,此類轉讓合同性質如何界定、效力如何確定、最后一手當事人如何救濟等均存在不同認識。現將此類案件典型裁判觀點羅列,希望引起對此類問題研究的興趣。
1.雙方并無主債務合同的事實,雙方之間簽訂的合同名為轉質權合同,實為買賣合同。轉讓人與受讓人對于車輛轉讓均有過錯,應各自承擔相應責任。
山東省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魯16民終216號判決認為,質押合同是出質人與質權人雙方基于主債務合同就質物擔保事項達成的書面擔保合同。本案中,訴訟雙方雖然簽訂的是《車輛轉(質)抵押協議》,但根據協議的內容及雙方并無主債務合同的事實,雙方之間簽訂的合同名為轉質權合同,實為買賣合同。
上訴人王慶帥從事經營二手車業務,明知涉案車輛頂賬而來,在無車輛行車手續的情況下,出賣給被上訴人孟令謙,致使該車因第三人主張權利導致上訴人失去所有權,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被上訴人孟令謙在明知車輛頂賬而來,車輛登記車主非上訴人的情況下,未對涉案車輛行車手續等基本信息等情況進行核實了解,亦存在過錯,但兩相比較,上訴人過錯明顯大于被上訴人過錯。上訴人應承擔主要責任,被上訴人承擔次要責任。雙方按照8:2確定為宜。
2.質權人與受讓人之間簽訂的汽車債權轉押協議,實為質權人對質物的轉質押,在質權存續期間,因該車輛按揭的原因,被相關權利人扣押,受讓人失去對質物的占有,雙方訂立的轉質押的合同目的不能實現,受讓人訴請解除轉質押協議,應予支持。
河北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冀10民終439號判決認為,蘇國占與出質人馬玉嬌簽訂的車輛抵(質)押協議中約定了甲方(馬玉嬌)保證如到期不能贖回,乙方(蘇國占)擁有該車的使用權和轉(質)押權,按揭期滿后擁有所有權。涉案車輛的質押期限是2015年7月2日至2015年8月1日。到期后,出質人馬玉嬌未回贖該車輛。
蘇國占與田連成之間簽訂的汽車債權轉押協議,實為質權人蘇國占對質物的轉質押。因出質人馬玉嬌同意質權人蘇國占到期后可以轉質押,質權人蘇國占為自己對田連成的3.6萬元債務,在涉案車輛上設定了新的質權,此做法不違反蘇國占與馬玉嬌的約定,亦被相關法律所允許。而在蘇國占與田連成的質權存續期間,因該車輛按揭的原因,被相關權利人扣押。田連成失去對質物的占有,其與蘇國占訂立轉質押的合同目的不能實現。故田連成訴請解除與蘇國占的轉質押協議,應予支持。
3.當事人之間簽訂的《車輛轉押協議》應當認定雙方間是買賣關系,在車輛抵押權人追及的情況下,受讓人以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還價款,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條件,法院予以支持。
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遼01民終11019號判決認為:雖然劉漢偉在一審的訴訟請求是要求鄒凱、李曉輝償還借款249,000元,但是在一、二審法院審理中,雙方均確認雙方間不是借款合同關系,故本案不能認定雙方存在借款合同關系。雖然雙方在轉讓該車輛時簽訂了一份《車輛轉押協議》,但是根據雙方在一、二審提供的證據及庭審中的陳述意見看,劉漢偉是想以低于市場價一半的價格購買該車輛的使用權;而鄒凱、李曉輝是做當鋪生意的,他們是從胡先龍處以二十三、四萬元的價格受讓了車輛,并獲取了相關質押資料后,再加價出賣給劉漢偉,并將相關質押資料一并轉移給劉漢偉,且在一、二審中均主張是以低于市場價一半的價格將該車輛的使用權轉賣給劉漢偉,因此應當認定雙方間是兩手車買賣關系。
關于該《車輛轉押協議》應否予以解除或撤銷的問題,本院認為,劉漢偉在受讓該車輛后不久,該車輛就被西安駿輝開走,雖然該公司在未經生效裁判或相關機關認定、公權力介入的情況下將車輛開走,其行使追償權的方式不當,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十九條“同一財產法定登記的抵押權與質權并存時,抵押權人優先于質權人受償”的規定,工商銀行長纓支行所享有的以該車輛優先受償的權利是法律賦予的,無論通過民事訴訟,還是其他途徑,其終將優于本案的雙方當事人受到法律保護。
而鄒凱在將車輛轉讓給劉漢偉之前,其已調查了該車輛的相關情況,已得知該車輛抵押給了工商銀行西安長纓支行,再結合鄒凱和李曉輝“是做當鋪生意和做債權轉讓生意”的自認,應當推定二人對該車輛存在一個合法的、優先于質權的擔保物權是清楚和知曉的,那么在向劉漢偉流轉該車輛時,其應當如實向劉漢偉告知該事實,善盡權利瑕疵的披露義務。
但是,雖然在一、二審法院中,二人均辯稱已向劉漢偉披露了該車已抵押給銀行的事實,但截止本院二審法庭辯論終結時,鄒凱和李曉輝也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其這一主張,故本院無法認定鄒凱和李曉輝取得該車輛后,又善意地與劉漢偉簽訂《車輛轉押協議》,將車輛流轉給劉漢偉。在車輛被搶走四個月的時候,劉漢偉提起本案訴訟,以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還價款,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一款(四)項所規定的合同法定解除的條件,本院予以支持。至于現在該車輛被追及、不能返還,并不是劉漢偉的過錯所致,故本案不能因車輛不能返還,而對劉漢偉的訴訟請求予以駁回。
4.由于在簽訂車輛轉押協議前,當事人間無債權債務關系,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轉質押合同關系,車輛轉質押協議的真實目的為買賣涉案車輛,涉案名為車輛轉押實為車輛買賣的協議應為有效。在涉案車輛無法向買受人交付時,轉讓人應賠償受讓人因購車產生的購車款及保險費損失。
甘肅省天水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甘05民終831號判決認為,轉質指的是質權人在質權存續期間,為擔保自己的債務,以其所占有的質物,為第三人設定質權的行為。本案中,在簽訂車輛轉押協議前,胡某、恒信車行與王某3之間無債權債務關系,無需將涉案車輛質押給王某3進行債務履行擔保,因此本案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轉質押合同關系,結合涉案車輛轉押協議的內容及當事人庭審陳述,應當認定王某3與胡某代表恒信車行簽訂車輛轉質押協議的真實目的為買賣涉案車輛,因此本案案由應確定為買賣合同糾紛,處理糾紛也應適用關于買賣合同的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而非關于質押的法律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雖然無證據證實恒信車行擁有對涉案車輛的合法占有、使用及處分的權利,但依據前款規定,涉案名為車輛轉押實為車輛買賣的協議應為有效。在涉案車輛被江蘇省句容市人民法院依法扣押并被裁定抵償給案外債權人的情況下,恒信車行無法向買受人王某3交付符合交易目的的車輛,未盡到全面履行合同的義務。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條”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的規定,恒信車行應賠償王某3因購車產生的購車款及保險費損失。
5.車輛轉質的,將車輛交付受讓人,車輛的質權自車輛交付時生效,在該車輛設定的抵押權因沒有辦理抵押登記,該抵押權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抵押權人擅自獲取并處分質物的行為,侵犯了質權受讓人合法權利,依法負有返還原物的義務,在原物不能返還的情況下,應承擔賠償責任。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津01民終8587號判決認為,涉訴車輛系紀海軍所有。紀海軍以涉訴車輛為質物,與案外人韓海洲簽訂質押借款合同。合同約定紀海軍到期不履行債務,韓海洲可以以轉質方式實現債權。后紀海軍未依約履行債務,韓海洲以103000元將涉訴車輛轉質于劉衛濤,并將該車輛交付劉衛濤。劉衛濤關于訴爭車輛的質權自車輛交付時生效。關于天津利斯達汽車租賃有限公司對訴爭車輛主張的權利,從抵押權角度來看,因沒有辦理抵押登記,故其對訴爭車輛享有的抵押權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從質權角度來看,因出質人沒有交付質押財產而未生效。
所以,天津利斯達汽車租賃有限公司在劉衛濤合法占有質物的情況下,擅自獲取并處分質物的行為,沒有法律依據,侵犯了劉衛濤的合法權利,依法負有返還原物的義務,在原物不能返還的情況下,應承擔賠償責任。故劉衛濤主張天津利斯達汽車租賃有限公司賠償103000元損失的請求,一審法院予以支持并無不當。
6.當事人之間簽訂《車輛轉質協議》,但雙方當時并沒有債權債務關系,實際上是一種買賣關系,由于車輛被他人行使權利,出讓人應當賠償受讓人損失。
山西省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晉10民終2789號判決認為,2015年6月3日,上訴人秦誠、李慧生與被上訴人馮新榮簽訂《車輛轉質協議》,但雙方當時并沒有債權債務關系,實際上是一種買賣關系,原審定性本案為買賣合同關系正確。協議中約定,上訴人保證被上訴人正常使用車輛,正常審車,若原車主索要回車輛,上訴人賠償全部損失。2017年3月17日,偉明公司以替吳曉偉還車款174366.68元,該車所有權保留為由將涉案車輛扣走。由于被上訴人已支付上訴人車款107000元,現偉明公司將車扣回,按雙方約定,上訴人應當賠償被上訴人的損失。
7.雙方當事人之間并無主債權債務關系,也不存在擔保行為,雙方不能構成轉質行為,雙方交易的僅為車輛的使用權,并非所有權,法律關系仍屬買賣合同關系,雙方解除買賣合同后,受讓人應當全額返還購車款。
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晉02民終1786號判決認為,溫智與李中偉之間未簽訂書面合同,但溫智交付款項、李中偉交付車輛的行為,符合買賣合同的特征。李中偉主張雙方屬“轉質關系”,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轉質是指在質押期間,質權人以質物為第三人設立質權的行為,轉質行為屬擔保行為,而李中偉與溫智之間并無主債權債務關系,也不存在擔保行為,所以李中偉將車輛交付溫智的行為并非轉質行為。
經庭審查明,李中偉的真實意思是指溫智明知該車為質押車輛,所以雙方交易的僅為車輛的使用權,并非所有權,即李中偉是將質押車輛出賣給溫智使用,即便出賣的標的物存在特殊性——質押物,但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仍屬買賣合同關系,故一審法院認定雙方存在買賣合同關系,并確定本案案由為買賣合同糾紛并無不當。李中偉的該項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解除買賣合同后,李中偉是否應當全額返還購車款以及溫智是否應當支付車輛使用費的問題。李中偉主張溫智清楚該車的權利狀況,應自擔該車被收回的風險,但雙方對此未進行約定,李中偉亦不能有效證明其向溫智明示了相關內容,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七條規定,李中偉應當返還全部購車款。
8.由于機動車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按相關的法律法規到公安機關車輛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轉讓人在沒有得到案涉車主有效授權的情況下,與受讓人訂立《質押轉讓協議》將該車以“轉押”的形式轉讓給受讓人,違反法律規定,相關協議無效。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1民終13197號判決認為,高業豪與陳偉龍訂立《質押轉讓協議》《轉讓協議》時,雙方系知道案涉車輛的登記車主是謝少平而不是陳偉龍,該車(包括該車的相關證照)最初由登記車主以“抵押”的形式交給司馬靜后,經過多次轉手(轉押),最后由陳偉龍取得的。雖然案涉車輛交到陳偉龍手上并由其控制,由于機動車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按相關的法律法規到公安機關車輛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陳偉龍在沒有得到案涉車主謝少平的有效授權的情況下,與高業豪訂立《質押轉讓協議》《轉讓協議》再將該車以“轉押”的形式以“轉押價格7萬元”轉讓給高業豪,違反法律規定。
對此,一審法院確定《質押轉讓協議》《轉讓協議》無效,高業豪與陳偉龍對導致《質押轉讓協議》《轉讓協議》無效存在過錯,由此產生的責任由雙方分擔,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予以確認。由于高業豪已經無法將案涉車輛返還給陳偉龍,必然會造成陳偉龍的經濟損失,確定由高業豪賠償陳偉龍35000元人民幣的損失的數額,是恰當的,本院予以確認。
9.雙方簽訂的協議書雖為”車輛轉(質)抵押協議書”,但雙方沒有債權債務關系,轉質的基礎并不存在,實為車輛買賣合同,該車輛在受讓人實際控制下丟失不能要求轉讓人擔責。
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魯11民終1506號判決認為:上訴人王英軍與被上訴人季明明簽訂的車輛轉(質)抵押協議,其內容是將車輛進行轉質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十四條的規定,轉質押為質權人為擔保自己的債務以其所占有的質物為第三人設定質權,即原質權人對新質權人負有債務。
本案中,季明明與王英軍之間沒有債權債務關系,轉質的基礎并不存在,且雙方當事人在一審庭審中均認可雙方為車輛買賣合同關系,可以認定雙方簽訂的協議書雖為”車輛轉(質)抵押協議書”,實為車輛買賣合同,即王英軍出資34000元向季明明購買小型汽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出賣的標的物,應當屬于出賣人所有或者出賣人有權處分。”上述協議寫明胡秉旭為案涉車輛的真正所有者,其將車輛質押在季明明處,可見,季明明雖然對案涉車輛沒有所有權,但擁有處分權,且該協議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故王英軍關于季明明出售案涉車輛的行為違法的上訴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王英軍已按該協議支付給季明明購車款34000元,季明明也已將車輛交付給王英軍,雙方已履行了各自主要合同義務。季明明承諾擔保案涉車輛手續正規、真實有效,原碼原號,不是盜搶、租賃、走私套牌或牽涉其他刑事案件的車輛,無隱瞞的不良性質,現王英軍不能提供證據證實案涉車輛存在上述瑕疵,以及該車輛在其實際控制下丟失具有可以歸責于季明明的原因,故其要求季明明返還車款并支付相關費用,無事實和法律依據。
10.轉讓人對車輛即使無所有權和處分權,但《車輛轉(質)抵押協議》并不因此無效,案涉車輛已經被收回,雙方協議已無法履行,合同目的已無法實現,雙方簽訂的車輛買賣協議應予解除。
河南省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豫17民終3444號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黃政對案涉車輛無所有權和處分權,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其與劉佳簽訂的《車輛轉(質)抵押協議》并不因此無效,一審判決據此認定雙方簽訂的車輛買賣協議無效不當,應予糾正。黃政與劉佳簽訂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合同無效的法定情形,應為有效協議。案涉車輛已經被收回,雙方協議已無法履行,合同目的已無法實現,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四條規定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雙方簽訂的車輛買賣協議應予解除。
黃政未告知劉佳該車輛已抵押給銀行的事實,劉佳明知黃政對案涉車輛不享有所有權和處分權且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購買,雙方均存在一定過錯,且過錯責任相當,故合同解除后,雙方互不承擔違約責任。因合同解除,黃政應將其收取的車輛款53000元返還給劉佳,由于該車輛已經被收回,劉佳非因自身原因客觀上已無法將車輛返還給黃政,黃政可向相關民事主體另行主張。